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任金雯在其新著《情感时代》中,从情感视角出发,阐释现代小说在十八世纪兴起的过程。在接受《上海书评》专访时,她谈到了为何以理性自我标榜的“启蒙时代”能够被定义为“情感时代”,并结合时代背景,对理查逊、伊丽莎白·海伍德、菲尔丁、斯特恩、沃尔普尔、安·拉德克利夫等十八世纪的作家作品做出了精彩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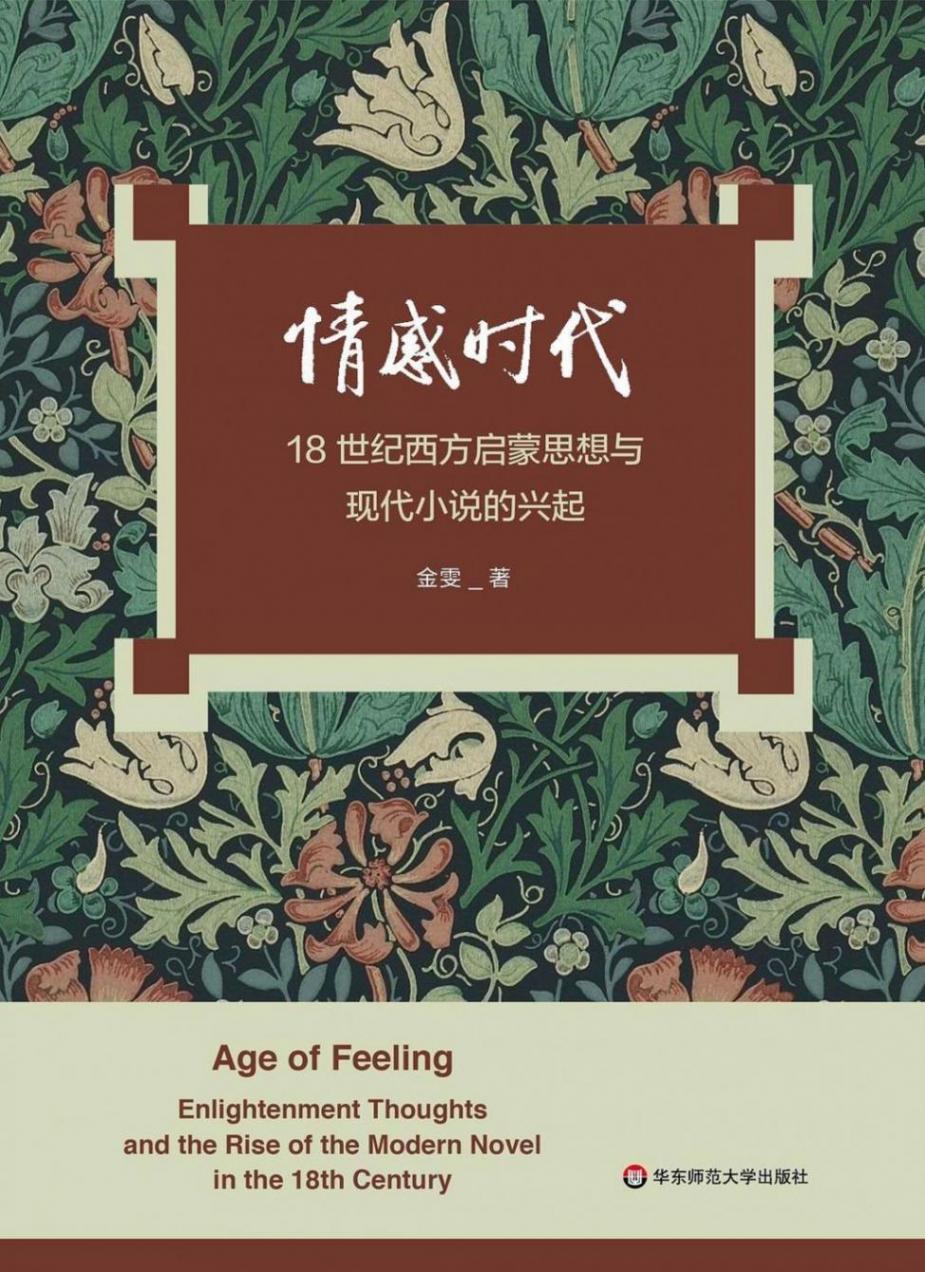
《情感时代》,金雯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1月出版,440页,95.00元
在《情感时代》的弁言和第一编中,您着重论述了人类情感被重新发现和定义的历程,并将我们耳熟能详的以理性自我标榜的十八世纪这个“启蒙时代”定义为“情感时代”。这个时代的来临,与西方现代文学的诞生过程——尤其是媒介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崛起——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联?
金雯:这首先关乎一个问题:社会何以成立?这是十八世纪的人们不断思考的一个问题,此时的西方历史来到了一个关键节点。具体而言,如果我们认为政治经济制度决定了整个社会机体的运行方式,到了十八世纪,随着宗教和政治权威的松动以及资本主义的兴起,人们为什么没有陷入对利益、权力的无限制的角逐?如果人们完全被工具理性推动,社会就无法成立,而是会像反乌托邦小说刻画的那样,进入霍布斯所说的“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或少数人掌控大部分资源、压迫绝大部分人的末日情景。但是,这些情况并非常态。这就让我们必须追问:究竟是什么力量对抗着末日的威胁?对十八世纪的思想家、文学家而言,他们自然也不愿看到这种情景。如何避免这种情景,如何缔造一种更为良性的社会秩序,如何使有利于社会建构的理念得到更好的传播和渗透,就成了关键的问题。在这场思考中,情感成为一个核心议题。其实,我们今天的情况也与之相似。现代社会长期处于“道德崩溃”的潜在危机之中,但这种危机始终没有全然压倒人类的“良知”,这与情感在社会关系中的角色是密不可分的。情感的力量和人们对情感的想象,为社会秩序的不断重建提供了支撑。
关于情感的作用这个问题,不同学者会从不同角度切入。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掀起了一股情感研究的热潮。例如,英国学者詹姆斯·穆伦就在他的研究之中,对感性(sensibility)如何转化为正面的社会价值做了追溯。他的研究中有一项创见:情感为什么会成为现代社会自发构建秩序的根基,人们为什么相信功利思维和理性计算不是人际交往的唯一原则,这并不仅仅是由于精英的观念在推动。从精英角度出发的研究,之前有过不少。例如,波考克在《德行、商业和历史》中,从观念史的角度探讨了早期资本主义对道德的需求,认为商业社会发展需要与古代德行不同的伦理规则。苏格兰启蒙思潮的代表人物亚当·斯密就在《道德情操论》中提出,是人类“同情”的能力使得商业社会能够自发形成秩序,正是以“同情”为中心的道德情操在资本主义发展中抵消了自利倾向的膨胀。然而,社会大众真的是在知识精英构建的资本主义伦理的感召之下变得富有同情能力和道德品质吗?这似乎与社会的实际状况是脱节的。
那么,普通人丰沛的情感世界从何而来呢?出版文化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当然,出版文化本身也是兴起于十六至十七世纪的印刷资本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它拥有相对独立的生命和逻辑。这里可以岔开来说一句,情感一直被认为是与理性算计相对立的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很早就被发现了。向前追溯,不管是古希腊的史诗还是中国的《诗经》,其实都描写了朴素、自发的情感会对人的所谓理性选择产生极大影响,这种对情感的重要性的认识贯穿了人类历史,例如莎士比亚很早就告诉我们,人的情感是一个谜团,李尔王的女儿就是不愿意说出“我爱你”,这种执拗的情感完全与一个人的生命利益相背离,就是因为人的理性不能抵抗情感的力量。但是,情感如果只是在少数识字者中传播,这种力量是不会有多强的。恰恰是由于出版文化的不断深入发展,情感得以借助于戏剧、小说等媒介广泛传播,脱离了识字者的小圈子,也不再局限于乡土和家庭的范围内。这就带来两个后果:一个是人们从媒介中看到的镜像越来越多,潜在的微妙情感得到全方位激发,另一个就是人们从媒介中增加了很多对生活可能性的想象。因此,人开始成为能够并且也想要去满足自身欲望的一种生物。戏剧表演作为一种重要媒介,可以越过阅读障碍,吸引不识字的观众。而出版物也是一种同等重要的媒介。从十五世纪中叶开始,随着印刷术的推广和出版物的增多,印刷资本主义为了追逐“流量”,无意间推动了意见的多元化——当时不仅涌现出取材于日常生活的各种虚构小故事,还出现了许多关于女性责任、女性生活方式以及女性社会地位等话题的讨论。这类内容,只要稍微识字就可以阅读。我在书中也举过一个例子,法国的纳瓦尔公主借鉴《十日谈》的形式创作了《七日谈》,通过男女间的故事和对话,让女性也拥有评判男性、做出道德判断的权利。这类故事促进了一个重大文化变迁,使得“罗曼司”(Romance)这个概念得到了扩充,不再仅仅指涉英雄史诗、骑士传奇,而是同时也包括浪漫化的言情故事。这样一来,罗曼司这个本来属于高雅文化的概念,就涵盖了更为日常、更加贴近大众的情感内容。就像塞万提斯在《堂吉诃德》中所展示的:象征着现代读者的堂吉诃德爱读的骑士传奇虽然在现实中逐渐沦为笑柄,但理想主义的骑士精神依旧具备强大的情感号召力。塞万提斯一方面批判、讽刺骑士传奇,另一方面也肯定了理想主义的情感感召力。而这种感召情感的能力也成了文学产业发展的基石。在媒介文化发展的大背景下,情感逐渐成为一个显性的议题和一股巨大的力量,人们可以不断地通过阅读小说、欣赏戏剧来反思和挖掘自己的情感,不断操演“同情”。当然,这种转变也得益于资本主义在欧洲不同地区的发展所导致的政治制度的松动。英国在内战之后形成了较为稳定的混合政体,在法国和德语地区君主制则没有受到明显的限制,而是呈现出君主与宗教权威、反君主与反宗教权威两股势力之间的激烈对抗。然而,无论在哪里,都出现了对传统政治权威的抵抗。在政治、经济因素的影响之下,加上媒介文化起到的关键作用,使人们开始关注如何顺应自身的欲望生活。
我在绪论开篇引用的《鲁滨逊漂流记》,就是一个典型案例。鲁滨逊的探险动机并不是为了追求财富积累或提升地位,而是一种内在的不安分。在笛福撰写《鲁滨逊漂流记》的十七世纪至十八世纪早期,已经开始流行各种探险小说,这种荒岛冒险的叙事并非笛福独创,笛福本人也受到这些文化潮流的影响,他笔下的鲁滨逊之所以选择远航冒险,并不是因为理性算计,而是出于难以清晰描述的内在的不安分。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十七、十八世纪的人们的生活原动力发生了根本改变——他们从自身的欲望和情感出发来规划自己的生活。恰恰是在这种情感成为生活原动力的语境之下,知识精英们才意识到,人们的行为深受情感驱动,进而开始思考如何在社会契约中赋予每个人更多的权利,以满足人的基本需求。像洛克、霍布斯这些人不仅是政治理论家,同时也是自然法理论家,他们注重从人性的角度来推演天然的道德原则。他们对政治制度的构想,建立在对人性和普遍道德准则的理解之上。这样一来,哲学家的首要任务就成了深入理解人性。只有这样,才能弄清人最基本的欲望和需求,进而设计出能够满足这些需求、促进人们相互的情感联结的社会制度。那么,这些需求到底是什么呢?对这些知识精英而言,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一是自我保全的需求,二是与他人建立联系的需求。十七、十八世纪自然法理论和政治哲学反复诉说着这两种需求之间达成平衡的可能和路径。

